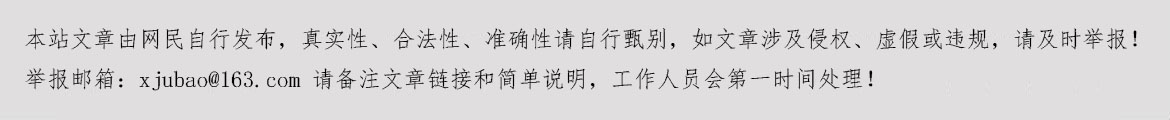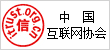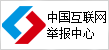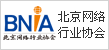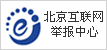我一直没有加入书法家协会,请当我是一直在练习写字的特务连文书
2023-02-20 14:26:09
意外的一等奖陈光建
字是敲门砖,这句话没有毛病。科举时代,阅卷考官对考生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写的字。字都写不抻抖,你要想他有好深的学问,一个字:玄!其实,书法就是按照规律写字,并不像有人说的那般神秘,而且与名利无关。不信?书圣王羲之的字,不是为参加展览,也不是为换钱而写的。但有一点必须说明,不读书而能将字写好,重庆话叫“空了吹”。
谈到写字,我以为“天资”一说,过于玄妙,一个人对事物的兴趣,不如将其看作是浸染的过程。上小学时,见师范毕业的母亲用柳体大字抄录的毛主席语录,整齐端正,心生好感,幻想长大也能写得如此好字。临到自己拿笔描红时,才知道要写好毛笔字绝非容易的事情。记得家里曾有一册赵孟頫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字帖,翻看时觉得这就是神仙写的字,太漂亮了。那些能写一笔功力扎实好字的人,大多是童子功,绝少半路出家者,而我们则错过了那种能从小练毛笔字的机会和环境。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大字描红,我的悟性不高,成绩一般都是三分。真正觉得应该好好练字,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成都五中,担任学生会宣传组长,负责办墙报之时。学校里有两位彼时“靠边站”的老师,一位写得一手斩钉截铁的魏碑,一定是临过龙门二十品中的《始平公造像记》。另一位则擅长行书,不知是临过苏东坡,还是赵孟頫的帖,结构紧凑,自成一格。学校大门内的告示栏里常能看到他们抄写的通知,或文件。心想,我的字能写到他们这样的水平就好了。碍于这两位老师的处境,我没有机会请教。与之相比,我那没有人指点,更没有临过帖的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宣传组有一位曾姓同学,估计是家里有人指导,能写隶书,书体是《曹全碑》。每次看他抄文章时,欲右先左,蚕头燕尾,潇洒而略带夸张的运笔,便心生羡慕。闲暇时,也照猫画虎地练习。那时字帖难求,也没有意识到临帖的重要。到一九七零年底参军入伍时,我已能写一笔美术体隶书。进藏途中,新兵连留给兵站的感谢信就是我的拙作。
当兵五年多,有近四年时间任文书一职。训练报告,奖励表格填写,年终工作总结,凡是涉及文字的事情,都是我的工作范围。连队的墙报,板报由我包干。按理说文书的字,在连里应该是写得好的,但我的字却属一般。说实话,战友中钢笔字写得比我好看的有好几位。近日,有战友找出我在特务连当文书时填写的嘉奖登记表和鉴定书的复印件图片,发到战友群里。我的天!上面的字体扭捏作态,惨不忍睹。里面还夹杂了一些二简字。当然,也留下了我玩的花样:美术体隶书的标题,和钢板体的字迹。当年,我主办的特务连墙报,曾获得团墙报评比的优秀奖,只是没有留下证明的照片。唯一保存的一张一九七四年春节拍摄的照片,背景黑板上的“恭贺新禧”四个字,以及右下角的“特务连”三个字,还能窥见彼时习字的痕迹。遗憾当时没有高人指点,审美水平得不到提高,而自我感觉却很良好,真是井蛙之见。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每年二月,团军务股复转办都会将我借去协助工作,原因就是我会写钢板体。这种字体源于在钢板上刻写蜡纸,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很适合填写退伍军人登记表和退伍证。三营七连文书,以及几位同年和七三年入伍的战友曾跟我学写这种字。现在想来,误人子弟啊!
上两图为作者任三十三团特务连文书时填写的奖励登记表
一九七六年退伍回成都,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外贸运输公司工作。期间,公司开会的会标,以及车队汽车门上印的“中国外运”几个字,都是我的作品。一九八零年夏,偶然经过古中市街,看到成都市青少年宫开办青年书法班的告示,在报名处犹豫徘徊时,负责招生的老师过来问我以前是否学过书法,我说学过隶书,他让我写了几个字,看后说还有些悟性。经他鼓励,我报了名,成为青少年宫第一届青年书法班的学员。教课的老师,后来都是四川书法界有名的人物。在书法班两年的业余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临习碑帖。一些著名碑帖,我都临过。临写并不是书法,但肯定是入门的必经途径。有一点必须明白,你临得再像,不过是复印字帖罢了。临帖,主要是体会和学习前人的用笔方法,字形结构,以及他的书写特征。自己的书写面目是你的取法,偏好和学识累积的自然外露,绝不是标新立异的信笔涂抹。正因为学书是一个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过程,许多聪明人耐不住这种枯燥和寂寞,中途放弃了。我们羡慕前人,使用毛笔写字是其常态,这使他们能够有大量的练习机会,随便一纸信札,都可能被今人视为作品和范本。也因为学书是一门科学,自有其规律,需要悟性,许多人穷其一生,却不得其门而入。
我的工作环境,大多与写字相关。先后任职的财会科,办公室,人事科,都需要书写。中午休息,就是我练习毛笔字的时间,寒暑不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而财会科的做账,办公室的起草工作总结,人事科的填写职工档案材料,正好提供了练习钢笔字的机会,真草隶篆我都临写过。临帖摹碑的过程,也使我有机会了解中国书法的演化历史,补了一部分字形起源,训诂方面的课。一九八八年,我参与编撰了由能源出版社出版的《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记选字》,这册字帖于一九八九年出版,后来多次再版,成为许多书法爱好者入门的教材。经过大量的书写练习,我的写字水平有了提高。在我离开外运公司多年以后,原财会科的同事告诉我,说是当年留下存档,由我经手填写的原始凭证,到了十五年期满,理应销毁,却因上面的字迹太漂亮,竟不忍毁掉,成了继任者的范本。
一九八八年九月,四川省省级机关举办首届硬笔书法比赛,有同事鼓动参加,我也报了名。因刚从江油出差回来,记得路过李白纪念馆时看到的一幅对联,便抄录下来作为参赛作品。时隔多年,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以致竟记不起是写的什么字体。作品塞在一个信封里托同事交上去后,便不再理会。心想,省级机关那么多写字高手,得奖的希望不大,重在参与吧。
比赛结束,果然没有音讯,连三等奖都没有人通知。时近年末,同事告知有一个一等奖没有人领取,上面姓名一栏填写了“光建”二字,是不是你喔?我联系到组委会,回复说是有一件作品,抄录李白纪念馆的一幅对联,作者落款“光建”。因装作品的信封遗失,不知作者单位,也不知作者的姓。评委一致认为字写得很好,不能因找不到人而埋没了,决定先评奖再找人。我报上姓名,领回了这个意外的一等奖。我不认识评委会里的任何人,那个年代也没有拉关系一说,评审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令人信服。
一个人的字写得漂亮,本身就是一种拿钱换不来的愉悦,倒真不在乎是否得奖。还是那句话,世上没有白吃的苦,当然,也没有随便能得的一等奖。我很怀念那些装在战友档案袋里,当年由我填写的材料,上面的字迹虽然幼稚,却是我想努力写好字的证明。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入书协,说我编的那册《颜真卿书麻姑仙坛记选字》和得的省级机关硬笔书法一等奖,已经足够申请会员资格。说实话,人生苦短,我自认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供虚耗,所以……,你就当我是一个一直在练习写字的特务连文书吧。在此,对关心我的人诚挚地说一声:谢谢了!
二零一八年日记一页
硬笔抄录唐诗
二零零三年为友人《桃花源记》隶书册署端
二零一九年冬至节临《曹全碑》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陈光建:四川成都人,祖籍安徽嘉山。1971年入伍,1976年退伍。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直属特务连文书兼军械员。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清远堂遗笺》一书作者,《印鉴-易均室辑拓印谱两种》特邀编委。《成都文物》,《文化成都》自由撰稿人。
作者:陈光建
电影下载 http://173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