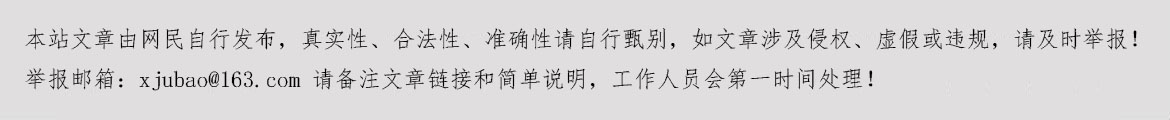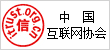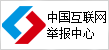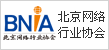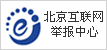我们听到的掌声、笑声与沉默,都可能不是真的
2022-12-28 10:12:02
观众是艺术家的衣食父母——所以,艺术家总得想法子影响他们的衣食父母。
据说,大喜剧家莫里哀每逢经常乔装打扮,去看自己的剧首演。还时不时左顾右盼卖萌不已:
“这个剧,啊,是哪个家伙写的啊?”企图把场面盘活一点,以免死气沉沉。
老年间京剧,叫好也有讲究。演员出场,最好有碰头彩;演员唱得好,行家的叫好能恰在点上,既能提示周围一起叫好,演员听了也舒服。
现场观众的反应很重要,往往能由此带动全场的氛围。
又不只是演出了。球场上,观众的反应也很重要。主场客场,虽有旅途劳顿之别,主要差别还是观众反应。观众的掌声,观众的嘘声,真能影响人。所以活力型球员,往往能带动气氛:观众会为一个飞身救球情绪高涨,樱木花道就曾经这样。
所以1970年代,ABA有个不成文规矩:每当J博士扣篮,对方教练会喊暂停,因为那一下子往往点燃全场,会让球员们心惊;暂停,冷一冷,让大家情绪过去再说。
所以十佳球是有价值的——点燃全场嘛!
1820年,巴黎有两位先生,索通与波奇尔。他们惯在歌剧院看剧,深知单个观众的反应,会如何影响周围。于是他们成立一个组织:
“歌剧演出成功保险公司”,专给歌手和剧院经理提供服务:
捧场服务。
说白了:
假掌声。
十年之后,捧场服务到了全盛期,成了全欧歌剧界公开的秘密:剧方付钱,观众鼓掌。
既然是服务,当然也得细化,甚至个性化。
到20世纪,意大利的捧场制度,已经分门别类,精雕细琢了,收费当然也有相应档次:演员登台时,男士给掌声和女士给掌声——类似于我们所谓碰头好——价格不同;演出时给寻常的“嗯这个不错”掌声,和长时间的“太牛了吧”鼓掌,价格不同。
如果要加喝彩声,得另外加钱;要求返场,甚或狂热的叫好喝彩,价格最高。
之所以不同的掌声价格也不同,是因为买这项服务的演员与剧方,深知不同的掌声,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也因为负责鼓掌的人们,早已通晓不同的反馈,会带来怎样的反应。
人就这么容易被影响。
有了广播与电视之后,现场鼓掌的业务没那么发达了——但别的行当,起来了。
现在我们看许多喜剧,都爱配罐头笑声。
到得后来,真假难辨,不知道哪段笑声是假,哪段笑声是真。
我曾反复揣摩,以为自己想明白了:
——某些隐晦的笑点,然而没笑声,所谓“包袱没响”,那这段剧的笑声,大概是真的。
——某些不好笑的笑点,依然出现笑声,所谓“不该笑的瞎笑”,那这段剧的笑声,大概是假的。
毕竟观众是人,不是机器;包袱又未必个个都响。
不是包袱都能笑出来,那是假笑;真包袱听不出来,却可能是真人吧?
但再了解深一点,就发现我还是想浅了。
罐头笑声这玩意,20世纪中期诞生于美国。
当然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些假掌声假笑声。比如20世纪中期,美国的制片人大卫·尼文觉得,罐头笑声这玩意,既狂野又不分青红皂白,相当机械,没劲!
但罐头笑声的大宗匠、CBS的录音师查理·道格拉斯认为:罐头笑声实在好,而且很有必要:从节目整体效果来看,罐头笑声有利于控制作品节奏。
——这大概就是“真实”与“效果”之争了吧?
道格拉斯先生发现:许多现场观众比较紧张,不容易笑出声;考虑到拍摄成本,现场收音,又远不如后期制作插入笑声来得方便。
于是1960年代,罐头笑声成了主流,许多编剧和导演,甚至专门留出台词之间的空白时段——有点像所谓让包袱——但不是方便观众们笑,而是方便制作方插入笑声。
就像意大利人为鼓掌喝彩分门别类似的,道格拉斯先生也不满足于一味傻笑。
1960年代,他专门通过各类剪辑,把罐头笑声专门细化了:
第一时间感受到笑点于是噗呲一乐的笑声,算是一类。
相对节制掩口轻笑的家庭主妇笑声,又算一类。
反应慢一点,但听大家笑了,于是自己也跟着笑的,又算一类——种种笑声混编起来,形成不同笑声,用来搭配各种包袱:
大众的、小众的、巧妙隐晦的、直白明显的,笑点。
是的,连假笑这玩意,都在六十年前被专门细化过。
真能以假乱真。
道格拉斯先生的罐头笑声,在1960年代盛极一时,但在1970年代后,走了下坡路。一是他的学生卡罗尔·普拉特捣腾出了更自然更柔和、不那么扑面而来的笑声,显得真实;二是那些表演者也越来越倾向现场有观众,觉得这样能有更积极的反馈,而不是自说自话;如果没有观众,也不用配假笑,因为真的很尴尬——当然这是后话了。
有趣的是,无论是被安排好的鼓掌声,还是被安排好的笑声,归根结底,都在向我们证明:
大多数人,无论自觉多么主动,终究是机械地按社会认同原理在行动。
只要周围笑得大声,就会情不自禁地笑得大声,即便不觉得好笑。
如果周围毫无反应,也就默默不动,哪怕内心波澜起伏。
用伦敦大学索菲·斯科特的说法:人每次发出笑声,都是在一个满是镜子的大厅里。
大概,笑声、鼓掌与沉默,本质都是人类社交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是制造出来,用来引导人的。
许多时候,周围看起来整齐的声音未必是真实的,只是大家都希望合群罢了。
哪怕真有人笑出来,也可能是假笑。
就像张爱玲《鸿鸾喜》结尾会说:一个与丈夫貌合神离的娄太太,因为听漏了丈夫不好笑的冷笑话,所以笑得最响。
我们所听到的掌声与笑声,或者我们感受到的沉默,都可能不是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