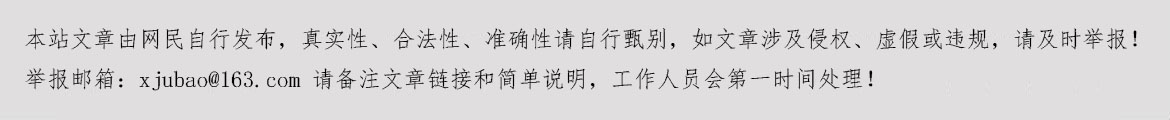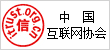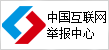一个香港小老板的深圳发家史:从工厂破产到带2000徒弟年产值40亿
2022-11-30 03:20:01
750室内空间设计-泉州商场专卖店铺设计-货架货柜展柜展示架定制-套房别墅自建房装修设计
1989年,深圳罗湖黄贝岭有一家小油画厂停工了。
这个小油画厂在黄贝岭建厂也不过才一年多时间,但厂房租金已经从2000多元飞涨到了4000多元,办厂的两个香港人觉得无力为继,索性不干了。
关厂之后,其中一个人心有不甘,决定去深圳关外找找机会从头再来。
他经过罗湖,穿过当年深圳最热闹繁华的布吉街,停在了一个叫大芬村的地方。
“深圳的西伯利亚。”这个香港商人看到大芬村第一眼时,轻轻说了这样一句话。
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全村加起来不到300个人,稀稀拉拉散乱建着几栋房子。没有房子的地方,只有臭水沟和芦苇丛。一条坑坑洼洼的沙土路,在偶尔路过一辆三轮车后尘土飞扬……
“但这真是一个办厂的好地方。”香港人又轻轻对自己说道。
靠近广深公路,荒芜但不偏僻;地处关外,来村里不需要办边防证,所以广州、东莞来帮忙的朋友出入便利;全村连一家商店都没有,更别说卡拉OK这种娱乐设施,所以很适合专心干活;最最重要的,是房租十分便宜……
这个香港人名字叫黄江,他生长于广州,于上世纪70年代“逃港”成了香港人。来深圳前,他一直在做“行画”生意。
行画,也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专用历史名词。最早是外国人发明的,和现在流行的说法“山寨”是一个意思,主要指山寨的世界名画。当然也不全是纯山寨,在山寨过程中经常会适当加入当前流行的元素。
1989年的黄江,站在大芬村头所有的权衡和考量,都是出于一个商人的本能精明和嗅觉。他只想再开一个油画厂,和他曾经在晋江、江门、广州和黄贝岭开的小厂差不多。
因为他也只是当时无数来内地的香港生意人中的一员,最关心的事只有成本和利润。
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这个选择,会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1989年农历八月十四,黄江带着20多个徒弟正式来到大芬村,用1600元租下了一个250平方的民房,并注册了“来料加工”性质的工厂。
大芬油画村历史上第一个油画厂,在这天诞生。有一位村民加入了这家工厂,每天去两公里以外的沙湾买菜,为工厂二十多号人做饭。
80年代深圳的“三来一补”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对当时的企业家优惠力度特别大,就拿行画来说,一张30块的油画,在当时的广州要交七八块钱的税,而在深圳只要两三块钱。
黄江又选中了大芬这片未开发的地方,使得他的油画厂成本大幅下降,利润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当初跟着黄江一起的画工们,看在眼里,动在心里,也开始了自己的规划。
渐渐地,大芬村自立门户的画工越来越多,新生的画室又需要大量新的画工,新人的不断加入也极大扩充了油画的风格和种类,整个村子生产油画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
越来越多的客户被吸引了过来,越来越多的油画订单飞了过来,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在1992到1995年间,已见雏形。
黄江说,生意最好的时候,他日夜不停督促两班倒的画工赶进度,经常站着看着就呼呼大睡了。所以经常为了提高效率画出更多的画,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办法。
1992年4月,黄江面对一个36万张油画的法国订单,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决定接单。数量实在太庞大,他发现不管怎么安排规划,都没法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出来。
反而是跟着他的画工他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他接单,“怕什么?”画工们拍着胸脯喊道。
多年以后,从黄江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个让人感动场景,我眼前仿佛依然能浮现出来那那一个个光着膀子的瘦弱身影,以及他们眼神和语气里无处不在的敢拼的劲头——
那是老一代深圳人特有的力量。
生意人黄江也不是等闲之辈,硬着头皮接下大单后,他另辟蹊径地在大芬开创了流水线作业:一幅画,分给十几个人来画,这个画天,那个画山,其他人按照不同的位置补水,树和其他景致。
这一个突发奇想的招数,效果简直立竿见影:一个人只专注画一样的东西,省去太多构思布局和调色准备的时间,重复地画还让手法越来越纯熟,质量无意间也突飞猛进。
据说负责验货的法国人,来到油画村,看着这惊为天人的世界名画流水线,惊讶得仿佛是面对着世界第九大奇迹,一边竖着大拇指一边激动大喊。
如果会中文他一定会“卧槽!卧槽!”地叫出声来。
当装着36万张油画货柜走出大芬村的那一刻,整个村子沸腾了,黄江在行画江湖声名远扬。
2000年,因为巨大的聚集效应,油画村的画廊和画厂接近300多家,整个大芬村的油画出口量占据了欧美市场的70%以上。
这个完全靠自身规模和效应自然形成的产业,以及在行业内取得的骄人成绩,成功引起了深圳市政府的注意。
正好这年深圳提出了“文化立市”的口号,市政府开始关注并服务起大芬油画村的产业发展。大量资金迅速投入,政府还出资购画帮助改善画工生存现状。
2002年开始,整个大芬油画村的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道路拓宽,广场扩建,破旧改造,以及画廊建筑外墙专业包装。仅菜市场迁移和空中电缆入地一项,就投入了1000多万元。
2004年,深圳举办了首届文博会,大芬油画村被指定为分会场。文博会之后,大芬油画村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这一年,大芬油画村的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
2005年,深圳对大芬村的支持和推广达到一个新高度,世博会深圳馆里面专门有一个大芬村馆区,现场展出高40多米、长7米多、由大芬500多名画工签名完成的巨幅《蒙娜丽莎》,效果极其震撼。
也是从这里开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深圳小城中村,开始打出了“世界油画中国大芬”的名片。
如同当年黄江的弟子们自立门户跟风师傅创业一样,福建莆田、厦门海仓等地也尝试学习大芬村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油画村,但似乎效果并不理想。
时势造就英雄,成功不是不能复制,只是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过去了,复制的成功便没有意义了。
大芬村十多年的飞速发展,除了形成了一条完备的行画产业链以外,也让无数人通过在这里的磨炼而创造了更多可能,实现了人生理想。
首先黄江自己就是这群人的杰出代表,一个默默无闻做着行画买卖的生意人,无意间创造了一个产业完备的新村,他自己成了“大芬油画村第一人”。
2004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油画村接见了黄江,赞许他“充分发动了民间力量,增加了出口活力。”
2011年正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油画村见黄江时,专门按照广东习俗给他封了个红包。
作为一个普通生意人,黄江在大芬油画村收获了一个生意人最高的殊荣。
很多广州美院、四川美院以及全国各地其他美术学院的学生,也慕名来到油画村,从最普通的画工做起,一步步积累和成长,有的成了黄江一样的画商,有的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现知名画家刘文全,最早就是黄江工厂里面的画工,曾经因为画风独特,黄江还专门给他单独作画作品单独出售的机会。
黄江说,在大芬油画村,称得上我徒弟的有一两千人,他们如今有的做着油画行业的生意,有的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
大芬油画村的村口,矗立着一栋典雅的黄色小楼,楼上匾额书写:黄江油画艺术广场。
这应该是对黄江最好的肯定了。
但凡来深圳超过两三年的人,都一定听过或者到过大芬油画村这个地方。
夹在布沙路和龙岗大道之间的一小片地方,“L”型的主通道从头到尾走路都不需要十分钟,以及主通道半包着的几排深圳城中村最常见的那种不超过八层高的农民房,便是它的全部。
而主通道拐角处的大芬美术馆,以及布沙路对面的卢浮宫、大芬油画交易广场和茂业书画交易广场,都是后来应油画村发展需要而建的。
不论是站在地铁3号线上或者飞驰在龙岗大道上,仅看大芬油画村的外表,平平无奇,和深圳其它城中村相比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甚至它的格局和规模比多数城中村都小得多。
布沙路那边的村口,倒是立着一只握着画笔的大手雕塑和一个斑驳的维纳斯雕像,村口对面的墙上,也有巨幅的“世界油画中国大芬”的广告牌。
这一切虽然并不能让人一下子联想起艺术,但至少是在倔强地向拥挤的车流人潮宣示:这里曾有过艺术!
如今的油画村,年产值已经突破了40亿元,但其实也正在面临着转型。
毕竟行画终究不是生存之道,艺术需要的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原创,终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还有,互联网的日新月异发展,也对油画村这种作坊式的商业模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加上疫情的限制,走向线上,早已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最后,是否,还会有当年人们像朝圣一样慕名而来?是否一直有新鲜的血液不断地注入,再形成新的效应?这真的很让人怀疑。
再走进那个车越来越多几乎占满了道路的村里,油画似乎正在远离。
或许是过于追逐产值的增长,商业化的过度发展,让艺术创作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亦或许是从前那种一群人光着膀子挥洒颜料的创作生产力太过于低端、已然无法满足订单越来越急迫的需求。
总之,油画村的角角落落里,忘我创作的场面越来越少,已经很难再找到2018年以前去时的情景:
路的两边,不远处就有一个画板,画板前面总会有个留着艺术家发型的瘦瘦男孩,光着膀子用颜料在画布上挥洒,而男孩的后面,往往会站着一个极美的女孩。
他们都不说话,女孩静静看着男孩,他们本身就像一幅油画,关于爱,关于梦想,也关于艺术……
有人站在满是铜臭的地上仰望星空,有人坐在艺术的宫殿里面倾听铜板叮当。
生活的真相,艺术的真谛,从来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也从来不是一句话,一件事,一种方式所能定义明白的。
但我们要相信奇迹。
深圳是一个每天都有无数奇迹被创造的城市,而由生意人黄江无意间创造的这个产业奇迹,无疑是最独特的一个。